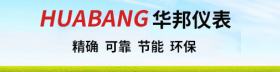光伏主材環(huán)節(jié)已經(jīng)卷無可卷,跨界風(fēng)儲(chǔ)氫成為企業(yè)競爭的第二陣地。光儲(chǔ)不分家,在光伏業(yè)內(nèi)已成共識(shí)。
多年來,光伏企業(yè)始終沒有放棄對儲(chǔ)能的執(zhí)著。世界范圍掀起“雙碳”風(fēng)浪后,儲(chǔ)能的海內(nèi)外市場迎來爆發(fā),超級(jí)賽道地位得到鞏固。
一時(shí)間,各大企業(yè)百舸爭流式的發(fā)展路線登上舞臺(tái),產(chǎn)業(yè)鏈在企業(yè)羽翼漸豐的過程中逐漸補(bǔ)齊。同樣的故事也發(fā)生在氫能領(lǐng)域。
業(yè)內(nèi)專家指出,到2050年,氫能在全球能源結(jié)構(gòu)中占比會(huì)超過12%,全球氫能需求將從當(dāng)下的8千萬噸/年增加到5.36億噸/年。
中國氫能聯(lián)盟則預(yù)測,氫能在中國能源結(jié)構(gòu)中的占比將在彼時(shí)達(dá)到10%。
氫能的美好未來吸引了大批量企業(yè)未雨綢繆。這場跨界之旅是篤定,還是試水?
錦上添花
從跨界時(shí)間來看,光伏主材企業(yè)的跨界更像錦上添花,跨界時(shí)間多集中在2020-2022的光伏發(fā)展黃金期。

隆基綠能號(hào)稱“光伏茅”,近年來除了在光伏各環(huán)節(jié)實(shí)現(xiàn)了產(chǎn)能布局,完成了產(chǎn)能一體化進(jìn)程,更在氫能提前埋下伏筆。
公開信息顯示,2018年隆基開始了對氫能產(chǎn)業(yè)鏈的研究,經(jīng)過三年技術(shù)積累,2021年3月31日隆基與上海朱雀投資,合資成立在西安正式成立隆基氫能科技有限公司。
這家上海朱雀投資大有來頭,近年來頻頻出現(xiàn)在新能源業(yè)務(wù)線中,近日朱雀投資再次攜手陜西建工、長安匯通、森特股份成立新能源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公司。
據(jù)介紹,目前隆基氫能主要業(yè)務(wù)范圍涵蓋電解水制氫設(shè)備制造和可再生能源制氫系統(tǒng)解決方案。氫能裝備作為隆基綠能五大業(yè)務(wù)板塊之一,與其他四大板塊共同形成支撐全球零碳發(fā)展的“綠電”+“綠氫”方案能力。
隆基在今年10月的投資者互動(dòng)平臺(tái)上透露,2022年隆基電解槽產(chǎn)能已經(jīng)高達(dá)1.5GW,今年上半年出貨電解槽17臺(tái)。
李振國曾經(jīng)在采訪中透露,“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現(xiàn)在有42%來自電力系統(tǒng),但還有很大一部分碳排放不與電力直接相關(guān),比如能源化工體系。綠氫作為二次能源引入,是一件必需的事情。”
對氫的參與環(huán)節(jié),李振國表示,隆基會(huì)繼續(xù)保持氫在應(yīng)用環(huán)節(jié)的研究能力,同時(shí)建立電解水制氫裝備、技術(shù)和服務(wù)的能力。
盡管,隆基在氫能做得有聲有色,但不得不承認(rèn)這是一筆未知的投資。即便是老牌氫能企業(yè)在2022年依然有尚未盈利的情況。

這一選擇與隆基一貫堅(jiān)持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原則有關(guān)。在最近的組件出貨量來看,隆基卻并不急于出貨,目前已滑落第一出貨量寶座。
原因在于,當(dāng)友商選擇布局TOPCon技術(shù)路線時(shí),隆基選擇了一條足夠長遠(yuǎn),卻幾乎注定坎坷的路,BC技術(shù)路線。


值得一提的是,在跨界氫能的布局中,天合光能、安泰新能、陽光電源同樣選擇了向制氫設(shè)備等技術(shù)含量較高的領(lǐng)域進(jìn)發(fā),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其中,正泰氫能攜手重塑集團(tuán)重磅發(fā)布已經(jīng)取得的氫能技術(shù)成果,包括綠氫制造裝備及兆瓦級(jí)氫能發(fā)電系統(tǒng)等核心技術(shù);天合光能步伐較快,今年年初宣布?jí)A性電解槽設(shè)備已經(jīng)進(jìn)入量產(chǎn)階段,目前已斬獲訂單。
而晶科、晶澳、協(xié)鑫則選擇投身制氫環(huán)節(jié),也就是用光伏產(chǎn)的綠電為制氫提供能源等技術(shù)要求相對不高的環(huán)節(jié)。
例如,協(xié)鑫在7月29日正式發(fā)布了上市公司的氫能戰(zhàn)略。該戰(zhàn)略包括藍(lán)、綠氫兩部分:首期建成年產(chǎn)230萬噸合成氨,逐步擴(kuò)能至每年400萬噸生產(chǎn)規(guī)模,可供應(yīng)國內(nèi)70萬噸藍(lán)氫;計(jì)劃到2025年建設(shè)100座綜合能源站,達(dá)到40萬噸年產(chǎn)能。
儲(chǔ)能熱土
然而,氫并非光伏企業(yè)跨界的主戰(zhàn)場,更多光伏企業(yè)聚集在儲(chǔ)能行業(yè),例如晶科、東方日升、協(xié)鑫、華為、天合、陽光電源、固德威等。
2021年,在政策推動(dòng)下,“新能源+儲(chǔ)能”項(xiàng)目快速在全國范圍遍地開花,直接刺激了光伏企業(yè)進(jìn)軍儲(chǔ)能進(jìn)度。
但儲(chǔ)能行業(yè)壁壘極高,難以輕易突破,例如上游的鋰、鈷、鎳等資源稀缺,難以像光伏一樣通過布局硅料產(chǎn)能控制成本;技術(shù)層面復(fù)雜,如果說光伏業(yè)內(nèi)的轉(zhuǎn)換效率決定了企業(yè)產(chǎn)品的市場,那么儲(chǔ)能的電池能量密度則決定了儲(chǔ)能產(chǎn)品的市場;儲(chǔ)能市場形成時(shí)間較短,還沒有形成良好的市場機(jī)制,未來不確定性高。

種種原因下,光伏企業(yè)大批量涌入儲(chǔ)能行業(yè),卻行動(dòng)保守。
在跨界而來的光伏企業(yè)中,儲(chǔ)能業(yè)務(wù)最為出色的莫過于天合光能。
天合光能儲(chǔ)能業(yè)務(wù)布局得最早,2015年天合儲(chǔ)能成立,2021年將市場擴(kuò)展到海外,英、美、澳為其主要目標(biāo)市場。
據(jù)官網(wǎng)信息顯示,目前天合儲(chǔ)能的產(chǎn)品包括液冷戶外電池柜、非步入式儲(chǔ)能電池艙系統(tǒng)、電池系統(tǒng),業(yè)務(wù)范圍覆蓋新能源側(cè)儲(chǔ)能、用戶側(cè)儲(chǔ)能、電網(wǎng)側(cè)儲(chǔ)能及微電網(wǎng)儲(chǔ)能等。
經(jīng)過多年發(fā)展,2022年,天合的儲(chǔ)能業(yè)務(wù),成為業(yè)績增長第二曲線,其攬獲儲(chǔ)能系統(tǒng)國內(nèi)出貨量排位第四名,全球出貨量排位第六名的佳績。
中銀證券報(bào)告顯示,2022年天合儲(chǔ)能國內(nèi)出貨量超過1.5GWh,全球出貨量近2GWh,成功交付國內(nèi)單體800MWh儲(chǔ)能項(xiàng)目。
2023年,天合儲(chǔ)能加速開拓海外市場,6月首個(gè)海外百兆瓦級(jí)儲(chǔ)能項(xiàng)目順利發(fā)貨,將為英格蘭北部建設(shè)容量為50MW/102MWh的儲(chǔ)能系統(tǒng)。
另外,2022年,天合儲(chǔ)能(滁州)有限公司宣布,擬投資45億元在滁州經(jīng)濟(jì)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新建年產(chǎn)12GWh儲(chǔ)能電池項(xiàng)目,包括3條磷酸鐵鋰電池電芯生產(chǎn)線和2條成套儲(chǔ)能產(chǎn)品生產(chǎn)線,年生產(chǎn)總產(chǎn)能為12GWh,其中6GWh電芯作為電池直接銷售,6GWh電芯在內(nèi)部生產(chǎn)為PACK模組后再加工成儲(chǔ)能系統(tǒng)銷售。
然而,即便是天合光能擁有8年的經(jīng)驗(yàn)積累,也不過剛剛停止虧損。其中2020、2021每年虧損超過1000萬元。
晶科、協(xié)鑫也頗有野心,選擇了硬吃儲(chǔ)能核心業(yè)務(wù)。公開信息顯示,晶科能源2020年開始進(jìn)軍儲(chǔ)能,2021年與寧德時(shí)代,國軒高科、贛鋒鋰業(yè)分別簽署合作協(xié)議,深入開展儲(chǔ)能布局。
直到2022年,晶科才開始成立儲(chǔ)能業(yè)務(wù)公司。據(jù)晶科能源2021年年報(bào)顯示,晶科能源首先選擇了打開家庭戶用以及工商業(yè)儲(chǔ)能的市場渠道,重點(diǎn)包括中國、中東非、東南亞、北美、澳洲與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晶科能源把目光放到了儲(chǔ)能業(yè)務(wù)的核心——電池。今年4月,晶科在浙江海寧成立注冊資本金為10億元的浙江晶科儲(chǔ)能有限公司,該公司名下年產(chǎn)12GWh儲(chǔ)能系統(tǒng)與儲(chǔ)能電池項(xiàng)目也在今年7月份舉行了開工儀式,該儲(chǔ)能項(xiàng)目總投資約52億元。
在半年報(bào)中,晶科能源提到,依托自身在光伏行業(yè)的生產(chǎn)和渠道優(yōu)勢布局儲(chǔ)能領(lǐng)域,公司創(chuàng)新光儲(chǔ)一體化系統(tǒng)解決方案, 并在光伏建筑一體化(BIPV)領(lǐng)域不斷開拓,致力于成為綜合解決方案供應(yīng)商。
今年6月,協(xié)鑫集團(tuán)與珠海市政府簽署合作協(xié)議,推動(dòng)儲(chǔ)能電芯、儲(chǔ)能PACK電池、移動(dòng)能源等領(lǐng)域合作。
其中,協(xié)鑫集團(tuán)將在珠海布局40GWh儲(chǔ)能電芯項(xiàng)目。今
年7月協(xié)鑫集團(tuán)旗下年產(chǎn)36萬噸磷酸鐵鋰儲(chǔ)能材料項(xiàng)目一期投產(chǎn),一期生產(chǎn)12萬噸磷酸鐵鋰儲(chǔ)能材料,到2024年,整個(gè)項(xiàng)目36萬噸磷酸鐵鋰儲(chǔ)能材料產(chǎn)線將全面達(dá)產(chǎn)。以晶澳科技為代表的光伏企業(yè)跨界則顯得不夠“從容”。
晶澳科技則選擇了與海博思創(chuàng)成立了合資公司,目前晶澳主要提供戶用儲(chǔ)能系統(tǒng)、工商業(yè)儲(chǔ)能系統(tǒng)、源網(wǎng)側(cè)儲(chǔ)能系統(tǒng)等解決方案,而不涉及電池產(chǎn)能。從技術(shù)層面來看,目前仍然缺乏核心競爭力。
東方日升則是通過收購公司進(jìn)軍儲(chǔ)能板塊,2018年,東方日升收購雙一力,在東方日升的加持下,2022年,雙一力儲(chǔ)能全球累計(jì)出貨量超過1GWh,同比增速超500%。
然而,東方日升目前正面臨著,主營業(yè)務(wù)異質(zhì)結(jié)技術(shù)路線表現(xiàn)不佳的情況。
未來前景
無論是氫還是儲(chǔ)能,都可以為光伏發(fā)電等新能源解決消納問題。光儲(chǔ)氫協(xié)同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業(yè)內(nèi)熱點(diǎn)。
據(jù)2021上半年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光伏產(chǎn)業(yè)棄光約為0.6億千瓦時(shí),平均棄光率2.1%。
彼時(shí)有業(yè)內(nèi)人士預(yù)計(jì),2年內(nèi),隨著光伏氫、儲(chǔ)能項(xiàng)目的落地,全國棄光平均棄光率有望進(jìn)一步下降。
截止至2022年光伏發(fā)電利用率已經(jīng)高達(dá)98.3%。隨著光伏裝機(jī)量的不斷提高,氫、儲(chǔ)需求不斷提升。光伏市場波動(dòng)程度受政策影響大,無論是裝機(jī)補(bǔ)貼,還是“531”新政,裝機(jī)量都有明顯起伏。
事實(shí)上,風(fēng)光儲(chǔ)氫都面臨著這一情況。
今年3月,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lián)合印發(fā)《“十四五”新型儲(chǔ)能發(fā)展實(shí)施方案》。
《方案》將新型儲(chǔ)能定位為構(gòu)建新型電力系統(tǒng)的重要技術(shù)和基礎(chǔ)裝備。《方案》提出,到2025年,新型儲(chǔ)能由商業(yè)化初期步入規(guī)模化發(fā)展階段,具備大規(guī)模商業(yè)化應(yīng)用條件。另外,氫能業(yè)務(wù)也在政策中嘗到了定心丸。
近年來,氫能產(chǎn)業(yè)政策密集出臺(tái)。
有媒體梳理,僅十四五以來就出臺(tái)了《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完整準(zhǔn)確全面貫徹新發(fā)展理念做好碳達(dá)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 明確統(tǒng)籌推進(jìn)氫能“制儲(chǔ)輸用”全鏈條發(fā)展;《“十四五”現(xiàn)代能源體系規(guī)劃》對氫能技術(shù)創(chuàng)新、示范應(yīng)用等進(jìn)行部署;《氫能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中長期規(guī)劃(2021—2035年)》對當(dāng)前和未來一段時(shí)間氫能產(chǎn)業(yè)發(fā)展作出了系統(tǒng)部署。
同時(shí),地方政府積極布局氫能產(chǎn)業(yè)。
目前,上海、北京、山東、重慶、天津等10余個(gè)省份已發(fā)布規(guī)劃,為氫能發(fā)展提供了扶持,為企業(yè)提供了生存土壤。
不過,光伏企業(yè)的跨界或面臨著雙重過剩的局面。光伏企業(yè)目前正受困于產(chǎn)能過剩,第三季度業(yè)績增速放緩。
儲(chǔ)能環(huán)節(jié)作為不輸給光伏的熱門賽道同樣面臨這一問題,據(jù)天眼查數(shù)據(jù)目前儲(chǔ)能相關(guān)企業(yè)已經(jīng)超過10萬家,僅今年新注冊企業(yè)就超過5萬家。
高工產(chǎn)業(yè)研究院的數(shù)據(jù)顯示,由于賽道過熱,產(chǎn)能增速明顯,當(dāng)前國內(nèi)儲(chǔ)能電池產(chǎn)能已超200GWh,整體產(chǎn)能利用率從去年的87%狂跌至當(dāng)前的50%,而戶儲(chǔ)電池產(chǎn)能利用率不足三成。
儲(chǔ)能這邊并不風(fēng)景獨(d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