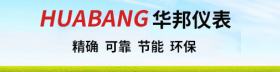根據(jù)規(guī)制經濟學理論,供電、供水、供氣等均屬于必須由政府規(guī)制的自然壟斷產品。其特點是:初次投入成本巨大,但隨著運營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其成本隨之降低,理論上可以趨近于零。
為什么會形成自然壟斷呢?理論認為:一是一般人投不起;二是許多涉及管網布設,重復布設意味著資源浪費;三是如果出現(xiàn)激烈競爭,則會兩敗俱傷,最終無人提供這些產品。
由于上述原因,在供電等產業(yè)領域往往自然形成一家或幾家生產者。為了避免自然壟斷廠商通過操控價格,制定“霸王”價格,攫取高額利潤,各國都對自然壟斷產業(yè)實行政府規(guī)制。規(guī)制的辦法主要有二:一是準入規(guī)制;二是價格規(guī)制。準入規(guī)制就是限定投資主體、投資規(guī)模和區(qū)域企業(yè)數(shù)量。
政府對電價規(guī)制,就是要限價。問題在于這個限價標準很難把握,價格定高了,用戶不滿意,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成本提高;價格定低了,電力企業(yè)要虧損,政府還得補貼,如果形成補貼依賴,企業(yè)效率就會下降。最理想的價格標準就是用戶、供電企業(yè)均可以接受、政府也不需要補貼,且不會影響國民經濟的成本。
在實踐中,主要通過各方參加的價格聽證制度,各方通過協(xié)商,共同制定價格,甚至是討價還價或曰“多方博弈”。協(xié)商定價時,最難確定的就是企業(yè)的生產成本,對于其他兩方來說,信息是不對稱的。無論是按照平均成本,還是邊際成本都難以有效進行規(guī)制,于是就有了最高限價規(guī)制、公共利益規(guī)制理論、利益集團規(guī)制理論、激勵性規(guī)制理論、規(guī)制框架下的競爭理論等規(guī)制模式。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國家掀起了公共管理體制改革浪潮,對電力等自然壟斷產業(yè)紛紛實行引入競爭機制的改革。我國在1998年也開始了以“廠網分開,競價上網”為主要內容的電力改革,試圖在發(fā)電環(huán)節(jié)引入競爭機制,逐步實現(xiàn)“競價上網”。然而,由于電力體制改革面臨“政企不分、產權不清、體制不順、法律滯后”等問題,電力產業(yè)的市場結構沒有根本改變,電力成本居高不下,電價增長過快,集資辦電和多種電價的政策使得電力市場價格混亂,符合我國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電力監(jiān)管體系一直沒有建立,電力規(guī)制方式和手段滯后,難以適應電力市場快速發(fā)展的需要。
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電力的發(fā)展是迫于資源環(huán)境的壓力,以及建立“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要求發(fā)展起來的。近幾年發(fā)展迅猛,到2008年底,我國新能源占能源生產總量比重超過9%。2007年,我國太陽能產業(yè)規(guī)模已位居世界第一,是全球太陽能熱水器生產量和使用量最大的國家和重要的太陽能光伏電池生產國,2008年我國的太陽能產業(yè)在不利經濟形勢下仍保持了30%的高增長。截止到2008年底,中國累計風電裝機容量躍過1300萬千瓦大關、達到1324.22萬千瓦,風力發(fā)電能力排名世界第四。
盡管我國新能源電力發(fā)展迅速,但其發(fā)電成本仍然遠高于煤電,在“競價上網”的制度安排下,與煤電的價格競爭明顯處于劣勢。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應該綜合考慮。
首先,鼓勵消費者購買一定數(shù)量的綠色能源,以擴大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通過市場準入和上網優(yōu)惠,消除新能源電力在開發(fā)初期的市場準入障礙,建立行之有效的投融資機制。為了鼓勵新能源電力上網,電力公司需要將售電收入優(yōu)先付給私人風機和太陽能所有者。
其次,供電作為準公共品,政府要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責任,通過政府采購、價格補貼、稅收優(yōu)惠等措施,支持企業(yè)更多生產新能源電力,讓投資者加速成本回收,至少可以賺到平均利潤。
再次,對仍然占70%市場份額的煤電污染,要計算社會成本,即:計算治理這些污染需要花費的公共支出,可以通過征收排污稅進行補償,或直接用于支付新能源補貼,迫使煤電成本提高,使企業(yè)生產成本與社會成本一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政府補貼或支持的重點要放在研發(fā)方面。努力提高科技水平,逐步降低新能源發(fā)電成本,這是長久之計。這方面,丹麥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丹麥成立國家實驗室,支持風能研發(fā),風電成本下降迅速,20多年來已減少了4/5。1981年風電成本為每度電12克朗,1999年降到3克朗,現(xiàn)在降到0.3克朗左右;由于技術進步和成本優(yōu)化,今后5年內將再下降20%,接近化石燃料發(fā)電成本,從而可以和新建燃煤甚至燃氣電廠競爭。
我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風力、最充足的陽光,只要價格合理,綠色新能源成為我國發(fā)電主力軍的前景就會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