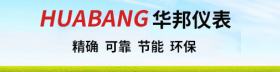他所指的“50萬輛”的目標,出現在新近出臺的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當中。這份歷時整整兩年的《規劃》(從2010年5月開始起草,到2012年6月28日印發)提出:“到2015年,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累計產銷量力爭達到50萬輛”。
可令人頗感意外的是,這份用工信部副部長蘇波的話說是“凝結了我們全社會和全行業的智慧”的《規劃》公布后,拍手叫好的人為數不多,記者在采訪中甚至聽到了許多質疑的聲音。
根據蘇波的闡釋,50萬輛的目標符合世界上新能源汽車發展的大趨勢。在《規劃》發布會上,蘇波講到:“歐美日本發達國家均提出了較大規模的未來五年和十年汽車發展目標,因此我們認為這個目標盡管相對較高,但對產業發展具有引導性、激勵性和挑戰性,相信通過各界的努力,我們爭取跳一跳,能夠達到接近或者完成這一目標。”
這個蘇部長所說的“跳一跳”,究竟意味著什么?根據中科院院士楊裕生的推算,若想完成2015年累計產銷50萬輛的目標,從今年起的未來四年內,年產銷量平均增幅必須達到132%。但根據蘇波的介紹,當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現狀是:核心技術尚未完全掌握;技術創新體系不健全;市場配套體系有待健全。而且,蘇波也承認,目前企業生產的電動車上市的不多,主要企業也只是在今明兩年陸續推出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50萬輛的目標距離現在只有三年半的時間,實現難度可見一斑。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在生產、消費、市場管理等多個方面,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有人站出來質疑:50萬輛,憑什么?
車企無車
一位不愿具名的上海新能源汽車示范運營負責人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目前上海新能源汽車的推廣瓶頸在車輛供應上,廠家的新能源汽車很難生產出來。例如,今年上汽榮威E50純電動汽車的目標是1000輛,但是能不能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不清楚,這個也不單單取決于上汽。因為上汽的新能源汽車配套電池、電機供應能否跟進到位,這很難說。”
本刊記者曾經通過南昌市科技局副局長胡向萍了解到,無車可買是曾南昌新能源汽車推廣初期的首要難題,但近期這種局面略有好轉。胡向萍告訴本刊記者,南昌本地車企江鈴生產的200輛純電動汽車今年年底有望下線。屆時,這批純電動汽車將駛上南昌街頭。但他同時表示:“車企產能與市場需求是緊密相關的,如果市場需求不大,新能源汽車產能一味擴張會影響到車企的生存發展,車企因此也不愿盲目擴張產能。”
事實上,國內大型車企在產能目標上放出超過萬輛的“豪言”為數不多。東風電動車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兆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到2015年,東風新能源汽車產能將達到5萬輛。但截至目前,東風的純電動汽車仍未量產,目標如何實現仍需要打個大大的問號。
北汽新能源總經理林逸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也曾表示:“北汽新能源單班年產2萬輛的整車車間已于去年8月正式投產。”但根據今年的實際情況看,產能大部分處于閑置狀態。
除此之外,一汽、奇瑞、比亞迪、眾泰等廠家的產能目標并未對外公布。而目前新能源乘用車銷量最多的江淮,今年雖然計劃推出4000輛同悅三代純電動汽車,但未來三年的產能計劃尚未對外公布,4000輛車何時能投放市場也不得而知。
配套政策制約發展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即使產能問題解決,隨著新能源汽車數量的增多,充電難的問題將會日益突顯。”在過去兩年內,諸如此類的“購車無處充電”、“充電站成擺設”等詰問經常見諸報端。例如南昌市紅谷大廈停車場附件的電動汽車充電樁成擺設,充電站成停車場;杭州數年前建的200個充電樁閑置;北京馬家樓充換電站閑置等等,此類新聞不絕于耳。
誠然,充電站先行為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其閑置時間明顯過長,反觀新能源汽車屬于快速發展產業,新產品不斷出現,新標準也在逐步的完善當中。曾經“先行”的充電設施隨著時間的推移恐難逃被迫廢棄的命運。
多個“十城千輛”試點城市的主管領導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強烈表達過“充換電設施應有統一標準、統一規劃”的意見。
有業內人士指出,《規劃》在新能源汽車數量上的目標可謂明確而具體,但在與之相配套的充電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卻僅以定性的文字描述,如:“根據新能源汽車產業化進程積極推進充電設施建設”,“科學確定建設規模和選址分布,適度超前建設,積極試行個人和公共停車位分散慢充等充電技術模式”等。
“何為積極推進?何為適度超前建設?”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拿著規劃文本質疑道。從新能源汽車示范運營初期至《規劃》發布的這幾年,新能源汽車與充電基礎設施建設“誰該先行”的爭論一直不絕于耳,規劃本身沒有解答這樣的疑問。
事實上,從2009年1月由科技部、財政部、發改委、工信部共同啟動“十城千輛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應用工程”(以下簡稱“十城千輛”)以來,這一問題早已露出端倪。“十城千輛”僅提到了在每個示范城市推出1000輛新能源汽車,卻同樣未提及與之相配套的充電基礎設施建設數量。新能源汽車與基礎設施相互制約也讓“十城千輛工程”提出的到2012年新能源汽車運營規模占到汽車市場份額10%的目標化為泡影。如今,《規劃》提出的目標遠遠超過了“十城千輛”目標,是否又會因為政策不配套而重蹈“十城千輛工程”的覆轍?
車價高 消費者不買單
完成50萬輛的產銷目標,最關鍵的問題是,即使在充換電設施完善,新能源汽車能夠買到的情況下,消費者是否就能接受新能源汽車?
目前,全國接待新能源汽車試乘試駕人數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嘉定國際汽車城。截止到2012年7月15日,該汽車城共接待試乘試駕人數20901人次。但記者驚訝的發現,在這個聚集了國內外14個新能源汽車品牌,建有387個充電樁、1座“加油+充電”站的國家級汽車城,到目前為止僅售出40余輛新能源汽車。“愿意試駕新能源汽車的很多,但由于售價過高,消費者目前難以承受”,一位汽車城工作人員這樣說。。
上海銷量低,在大多數人看來是因為上海補貼細則未出及車價過高所致。同為試點城市,在國家、地方政府、企業三方共同補貼下,合肥市目前江淮純電動汽車對私銷量達到1585輛。
在2010年首批推出的585輛江淮同悅一代純電動汽車中,江淮自己的員工購買了將近四百輛。“誰來吃這個‘螃蟹’?鮮有消費者愿意掏錢來嘗試”,江淮汽車技術中心產品規劃部工程師江敏說,“即使是螃蟹,也是多輪補貼之后的螃蟹”。
這批江淮同悅一代純電動汽車成本約為12萬元,最后出售的價格卻僅為4萬元左右。8萬元的降價幅度來自于國家提供的4.5萬元、地方政府提供1萬元及江淮提供的約3萬元補貼。但其后推出的1000輛同悅二代在價格上并未達到同悅一代的優惠額度,據一位江淮內部人員介紹,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的1萬元補貼取消了。
記者從合肥市政府了解到,合肥的補貼方式可能需要再次調整。有分析認為,目前地方政府補貼政策的調整可能與地方經濟下行有關,從去年開始,地方財政普遍吃緊,大額補貼并非可持續的選項。如果企業、地方政府的補貼不再提供,江淮純電動汽車的價格,將比現在搞出三萬元左右——“那時消費者能否接受就不好說了”,一位江淮內部人士表示。
“有市場需求的車不合法”
從目前各企業的產品報價來看即使補貼后,能降到江淮純電動汽車這樣低價的新能源汽車幾乎沒有。比亞迪純電動汽車補貼后售價仍高達24萬元,眾泰兩款純電動汽車的補貼后售價也超過10萬元。與此相對照的是,不需要補貼、不需要充換電設施支持的微型電動車近年來迅速興起,以其低價、充電方便、安全性好等特點迅速獲得了眾多消費者的青睞。
這是在整個電動車行業難得一見的景象。中國工程院院士郭孔輝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如果說要把微型電動車市場放開,這個算到電動車的目標里面,三年50萬都沒有問題。”
但制定《規劃》的四部委目前對于微型電動車態度仍未統一。有支持開放試點的聲音,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認為“讓微型電動車試點是較好的方式”。同時,也有堅決遏止的意見,發改委產業協調司副司長陳建國曾說“微型電動汽車不屬于新能源汽車,微型電動汽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于它的安全性達不到汽車的安全標準就不應該在機動車道上混行,它就應該有專用道,沒有專用道,那它就很難發展。”
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副院長劉剛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真正有市場前景的是微型電動汽車,這個潛在的市場應該有一億輛左右。而《規劃》提到的2015年50萬輛的目標,如果僅僅是按照目前示范運營的方式推廣,這種目標本身并無充分根據。”
劉剛還感嘆道:“目前沒有市場需求的車是合法的,有市場需求的車是不合法的。”這是他認為的中國電動汽車產業發展中最大的問題。因為從技術可行性和市場需求兩方面出發,微型電動車是最有前景的,卻受到了政策的限制。“我覺得整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思路,包括管理思路等都應該認真思考,這個思考方向很簡單,就是實事求是,尊重需求。”劉剛如是說。
根據記者的了解,目前山東省微型電動車的年產銷量約為7萬輛左右,年增長率約為40%。對于該增長率,劉剛表示目前無法評估,他認為目前的增長是在政策不支持情況下的增長,沒有實際意義。
江蘇益茂集團董事長陳恒龍對此持相同看法,他認為現在產銷量意義不大,如果政策支持,市場相對放開,益茂生產的微型電動車在山東和江蘇市場能各賣出30萬輛。山東省經信委副主任楊少軍也曾表示,如果國家允許微型電動車掛牌,將會創造一個十分巨大的市場,迅速培育起一個規模宏大的新興產業。
政策能否一視同仁?
即使市場潛力再大,消費者需求再強烈,“無法管理”這一個詞便足以扼殺這個產業。這里提到的“無法管理”,具體包括安全性達不到標準,微型電動車使用的鉛蓄電池回收無法管理等方面。
但記者在采訪支持微型電動車的專家以及相關企業時,聽到的更多的聲音是希望“被管理”,希望出臺具體的政策以尋求良性發展。劉剛分析說:“對電動車來說,電池回收是需要重視的問題,只要國家出臺相關的政策約束,比如誰生產誰回收,這些難題是能夠解決的。”
寶雅新能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周忠濱告訴記者,目前國內正在醞釀“短途純電動乘用車”的相關技術規范,這個標準是由工信部牽頭制定的。他表示:“對寶雅來說,如果未來出臺相關標準,我們是樂于接受的。在電池回收方面,我們會和電池供應廠商簽訂相關協議,這個事已經開始做了。” 陳恒龍同樣表示:“鉛酸電池回收的確是個大問題,我們要共同呼吁將回收工作落實。另外,鋰電池的回收也需要加強。如果有一個很全面、很系統的銷售體系和服務體系,目前的問題都能解決。”此外,他還提出:“在電池回收方面,我們希望和政府一起來做這項工作。”
除了“管理成本過高”外,“技術水準低、不符合產業發展方向”也是微型電動車遭遇政策瓶頸的主要原因。有關方面曾公開表示,山東生產的那些電動車是“垃圾產品”。
但陳恒龍并不認為微型電動車就意味著“技術水準低”。“我們生產的微型電動車是通過正規的汽車設計公司設計,完全能夠達到正碰和側碰的碰撞標準”,他說,“我們也會上齊四大工藝生產線,建立銷售和服務體系,傳統汽車企業有的,我們一樣也不差。我們不要財政補貼,不要特殊扶持,只要政策能夠做到一視同仁,給我們一個生產牌照,給我們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
這樣的呼吁由來已久,不知是否會因為“規劃”所提出的“2015年50萬輛”的目標,而使這些新興的民營企業獲得“證明自己的機會”?
在采訪中,山東一家微型電動車企業負責人的話讓人印象深刻:“不搞電動車,北汽、上汽活得好好的,而我們會死掉,所以砸鍋賣鐵也要搞。我不相信,等我們把規模和技術水平都搞上去了,政府會讓我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