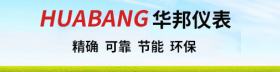60年代:為了收上電費幫人割豬草
1960年下半年,毛今延從衢州發電廠轉到衢州市區供電所做線路工。此時,衢州城區的電向外只通到市區西安門大橋下的一個村。在之后的三年時間里,城區附近的安仁、高家等地農村才先后通上了電。但當時的電力線路很簡陋,全是木頭桿子。
1963年,毛今延調到業務組,主要工作是裝表接電、收費。那時,市區范圍內只有2000多個用戶,市民用電計費還是“包燈制”,按每盞燈5毛錢一個月收取費用,發電廠也未能實現全天候供電,每到晚上12點就沒電可用了。
1964年開始,衢州市區開始合表用電,每個單元或幾個單元合并裝一個電表,按電表計量度數收取電費。作為業務組員工,在合表用電后,毛今延和他的同事們每月的工作內容增加了很多:每月的5號,抄表工們各自分好線路,再在自己線路范圍內抄表,然后回單位用算盤沒日沒夜地計算電費,之后再到各個村收取電費。“經常是一圈忙下來,就又到了下一個月的抄表收費時間。”
當時,他們整個業務組只有八九個人,要負責全市的電費收取工作,幾個女職工留在城里收電費,男職工則多被分到農村。毛今延當時的線路是市區――下張――安仁――全旺――大洲。每天早上6點出發,經常一圈跑完回來,都得晚上七八點了。
當時,收農村的電費非常困難。那時一個自然村只設立一個電表,因為農村線路損耗大,分派到戶的電費從幾毛錢到兩三塊不等,“經常有農民要靠賣雞蛋湊電費,費用很難收。”雖然當時一般是由當地村委代收費,但碰上始終湊不來錢的人家,他們也經常去幫助做工作,有時為了得到對方的支持,還要主動幫農民兄弟割豬草、割稻子。
“我印象中有一個特別敬業的同事,名叫鄭其樂,白天收不到電費,就晚上再去,不吃農民一餐飯,直到把錢收上來。”毛今延說。
當時正碰上文化大革命,他們的收費也有了新策略。為了做通農民思想工作積極配合收費,每次到一個地方,就請當地村委會幫助召集大家學習毛主席思想,誦讀《毛主席語錄》,然后再做工作收電費。“我們的一些女同志很能干,別人在開批斗大會,她們就跑上講壇,拿著欠費單宣讀欠費人的名字,當眾催繳電費,讓欠費人自慚形愧。”而在市區范圍,市民上門交費情況較好,收費率達到了100%。不過那時市區范圍一年的電費也就10來萬塊錢。
80年代:用空調要交使用費
到了80年代,衢州市區范圍內的用電戶逐步增加,有了1萬多戶。但居民用電依然受到限制,要裝空調,還需要到三電辦公室審批才能安裝。“裝一臺空調,除了要一次性交納380元的供配電貼費外,每年還得出500元的三電設備費。”毛今延說。為了防止有人偷裝空調或者不交費,每年都會有專人上街檢查,以發現漏網之魚。據毛今延介紹,“群眾辦電、安全用電、計劃用電”是那個年代的一大原則。每年到了4、5月份,就開始做用電計劃,把用電量分配好,主要還是保農村用電,一到農業灌溉的時候,城里很多單位就得拉閘限電。而且每到雙夏時節,電力部門還要組織小分隊下鄉,通過唱道情、放電影、寫標語的方式宣傳安全用電。農村用電收費標準分了好幾個檔次:“灌溉用電4分2一度,加工業8分,照明用電一毛五。”
如今:人人用電舒心了
“重發(電)輕供(電)不管用(電)”是早期電力工作的真實寫照。毛今延最大的感觸是,曾經簡單的管理收費,如今已經成為對客戶全方位的服務。“別的不用說了,就是居民家里出現一點小故障,一個電話,電力部門就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幫助解決。現在想啥時候用電都行,在我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衢州城里,每天晚上12點之后就沒電可用了。”
44載里,在電力部門多個崗位工作過的毛今延由衷地說:“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電力部門對管理、運行、營銷、服務等模式做了統一和規范,理念變了,服務客戶也更為優質和高效了,大家用電非常舒心啊。”據統計,特別是經過近二十來年的發展,衢州全社會用電量從1986年的13.79億千瓦時增長到2008年的85.31億千瓦時,僅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這一項,2008年的用電量就是1986年的16.73倍。